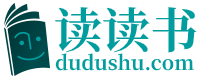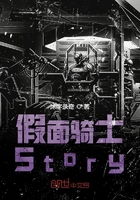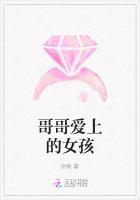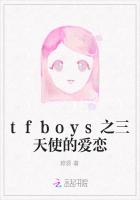但是,“重写文学史”操作起来却并非如此简单。难度首先在于,旨在颠覆以往评判标准的颠覆行为是否会牵连到对以往文学史著作描述的基本文学事实的颠覆?也就是说,虽然重写文学史力图颠覆的是旧文学史著作的文学史观,但新的文学史重建的基础是什么?比如,在文本选择问题上,如果它尊重旧文学史所选择的文本,那么这种重建先天的一个宿命就是它要部分地继承它本来力图颠覆的文学史观。因为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入文学史,这本身就包含了史家主观的价值判断,当然也就体现了史家的文学史观。反之,如果全盘推翻,重新选择文本,那么这种选择又面临着形成新的遮蔽的危险。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受到异议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在这部文学史著作中,陈思和先生完全推翻了以往文学史文本选择的惯例,“以往的文学史是以一个时代的公开出版物为讨论对象,把特定时代里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现象来讨论。我在本教材中所作的尝试是改变这一单一的文学观念,不仅讨论特定时代下公开出版的作品,也注意到同一时代的潜在写作……使原先显得贫乏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于是,在“潜在写作”概念的支撑下,作者挖掘出了一大批面孔陌生的文本,比如沈从文的《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绿原的《又一名哥伦布》、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等。作者将这些文本选入文学史的理由是,“虽然这些作品当时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发表,但它们确实在那个时代已经诞生了,实际上已经显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多层次的精神现象。”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些“潜在写作”文本的真实性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我们在此要讨论的是,陈思和的文本选择已经给十七年文学史写作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本选择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文本产生的社会效应,还是根据作家的精神现象?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表述:文学史家对文本的选择是侧重于读者,或者说是受众,还是侧重于作家,即创作主体?当然,这个问题同样也适合抛给整个文学史写作。陈思和对“潜在写作”的挖掘,显然说明他更加注重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这个层面,所以,他才会宁愿舍弃在当时产生过轰动效应的诸如《青春之歌》、《红岩》等“经典”文本。而以往的文学史著作进行文本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作品产生的社会影响,只有那些真正对当时读者发挥过作用的文本才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南京大学许志英先生认为:“在我看来,入不入文学史,主要看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有社会影响的可以入,看不出社会影响的,则可以不入。”在同一篇文章当中,许先生还回忆道:“记得1962年我参加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时,唐先生就什么样的作家可以入史问题,请示过周扬先生。周的回答是,哪个作家入不入史要看‘历史是否过得去’,譬如张资平当时被称为创造社的‘四大金刚’之一,不写他那段历史就过不去。以历史是否过得去为入史与否的标准,这是一个适用性很强的标准。”那么,我们不妨回头试问一下,这些“潜在写作”文本,有社会影响吗?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它们不进入历史,历史是否“过得去”?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所以要采取这种选本策略,我想主要是为了满足作者对“十七年”文学的一种美好的想象,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言:“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但是,在公开发表的作品当中又实在难以寻觅到这种“异端”声音,洪子诚先生曾经“为了寻找‘遗漏’的‘珠宝’,真花费了不少时间。翻过不少作品集、选集,各种过去的杂志,从《人民文学》,到许多重要省份的杂志。结果非常失望,好像并没有发现让人振奋的东西,或者说很少”。于是陈思和先生就只能将目光转向“潜在写作”。
那么这种将目光由读者转向作家的策略是否值得文学史写作借鉴和提倡呢?在何兆武、张文杰翻译的英国当代哲学家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的译序一中有这样一段话,也许会对我们眼前的这个问题有所启迪:“沃尔什又认为历史解释中就隐然地包含有对普遍真理的参照系,尽管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这一点并不是显然的、自觉的或有意识的,也就是说,要理解历史,我们就必须运用某些与之相关的普遍知识。”[]文学史无疑是历史的一个分支,作为理解历史的一种表现形式的文学史著作必须尊重大多数史家公认的“普遍知识”。否则,历史就会滑入相对主义的深渊,文学史写作也就失去了可能性。在“十七年”文学史写作中,我们可以将这种“普遍知识”理解为基本的文学事实,即史实。从对当时文学期刊等史料的考证来看,“十七年”文学的基本史实之一就是文学文本的“一元化”特征。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面世以来,之所以引发了众多的争议,就在于它破坏了大家公认的文学史实。
同时,“潜在写作”进入文学史,必然要对“显在写作”形成新的遮蔽。和“显在写作”对“潜在写作”的遮蔽相比,这种遮蔽的危险性显然要大得多,其后果就是误导后人对“十七年”文学基本风貌的把握,文学史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另外,对已有的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是近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比如陈思和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对《山乡巨变》、《锻炼锻炼》、《李双双》等作品中“民间隐形结构”的挖掘,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对《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等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等。除此之外,近年来在各类学术刊物上还涌现出了一大批致力于“重新解读”的文章,什么欲望叙事、女性视角、情爱主题、婚恋、性等等,都被从“十七年”文学的身上挖掘出来。可以说,对已有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是推进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任何作品经典化的过程都是对其进行不断阐释和解读的过程。“重新解读”是基础性的“量变”,“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形成“质变”,也就是对某一时段文学总体价值判断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十七年”文学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就现在而言,这种重新解读产生的观点还是不宜进入文学史写作。因为在“量变”还没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这种重新解读所产生的观点还没有在大多数学者中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新观点入史必然要对原来被广泛认可的观点形成遮蔽,而这种遮蔽很容易使一部文学史变为奇谈怪论。
三、“十七年”文学史写作的正途
对于“十七年”文学,无论是压缩、忽略以至于逐出文学史之门,还是挖掘“潜在写作”或者重新解读文本,其实从出发点上来讲都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对这段历史基本文学形态的厌恶,导致这种厌恶的理由可以是“一元化”、“政治化”,也可以是所谓的“虚假性”、“宣传性”等等,于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重建一种崭新的、可以满足我们期待的文学史就成为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他们的不同只在于操作路径上的差别。李杨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种观点:对“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要有文学史意识。“所谓‘文学史意识’,是与‘文学爱好者意识’相对应的。”意即,作为具有专业背景的文学史家,要区别于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不能以个人好恶(或者说是时代的好恶)来取舍裁决文学史。文学史家的理想姿态应该是客观与超然的。
但是,严格来讲,绝对的客观与超然对任何文学史家都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境界。“历史学家总是以自己的哲学观点在研究过去:这是无法改变的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前提假设。归根到底,主观的因素(无论先天的或后天的)总是无法排除的,这些因素可以呈现为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宗派性或任何其他的什么‘性’。”认为“十七年”文学并不“单一,苍白”,而是丰富多彩的,只不过是原来的文学史没有挖掘出来,这种想象不也是一种假设吗?这是否证明了这种想象的合理性,从而支持了我们前面指责过的文学史的写法呢?答案是否定的,果真如此,历史真的要成为一张任人涂抹的羊皮纸了。“历史”本身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它其实包括两个层面。“它包括(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2)我们现在用它们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洪子诚先生也指出过:“关于‘历史’这个概念的使用,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涵义。如80年代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中所说的,一是发生过的涉及、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口头的,或文字的),三是讲述者对于历史事件持有的观点,他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观点、态度、方法。后者也可以称为‘历史观’。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历史’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前二者。”两种“历史”的性质是迥异的,作为“发生过的”“事件”的“历史”是客观的,不会因人的认识和理解的介入而改变;而作为“这些事件的讲述”的“历史”则是主观的,可以因主体、时代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说,文学史家主观性的渗入只是在第二种“历史”所指中才是合法的。同时,第一种历史(以客观形式存在的历史)又对第二种历史(有主观因素介入的历史)形成巨大的约束和限制力量,从而使主观因素在其中不至于无限制地蔓延,否则历史就等同于虚构的艺术了。这一点恰恰构成了我们讨论“十七年”文学史写作问题的关键。
“十七年”文学史写作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史实出发,这才是文学史写作的正途。这里的史实,就是以史料形式留存下来的文学期刊、作品、作家传记、回忆录以及体制内的文件、记录等一切与文学有关的资料。所有这些史料综合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关于“十七年”文学基本的历史情境。这样的表述可能会遭到如下的质疑:“潜在写作”下产生的文本(假设其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难道不能作为文学史写作的出发点吗?这就涉及到我接下来要阐述的一个观点,即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都不是处在同一层面上的,“十七年”文学也不例外。
有很多学者主张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应用于当代文学史写作,这无疑是有积极的建设意义的。“他(福柯,引者注)要用‘考古’的方法,重新考察我们现在普遍被接受的知识、思想、信仰等被建构起来的过程。”“用福柯的术语说,就是要用‘系谱学’的方法,找到一层一层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深入地分析出“十七年”文学从产生到如今,是怎样一步一步被建构成我们眼前的这种形态的,它和历史的原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为什么我们就认为我们现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是客观公正、无可指摘的?但是,从性质上说,福柯的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历时性的考察。也就是说,以当下为起点,“一层一层地挖”,逐层向前追溯。它的重点不在于揭示事物的本真面貌,而在于揭示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都是哪些因素对这一过程发生了作用。
在此,我们不妨也借用福柯的“考古学”(archaeology)这一概念,但是,我们对它的使用却是在“共时”意义上的。稍有考古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任何历史时期的遗迹中,都是有些文物处在表层,而有些则处于隐层,或者说下一层,而在时间上来讲,它们却是同一时代的。对“十七年”文学来讲也是如此,所有的文学作品、作家、文学现象、思潮流派等等,不可能处在同一平面,有些是显在的,处于表层,有些是隐在的,处于隐层。诸如《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之类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个时代就是处在显层的作品,而具有分裂意义的“潜在写作”就是处在隐层。两者虽然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文学史家在将其入史的过程中,必须优先处理“表层结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而我们现在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往往根据自己的一厢情愿将显层置于隐层,或者将隐层置于显层。
既然在文学史写作中主观因素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主体思维方式的反思就是我们在“十七年”文学史写作中必须要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在这里,有两种思维方式尤其需要检讨,一种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一种是不顾历史情境、随意臆测历史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一直是我们深恶痛绝并力图摆脱的,但是遗憾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始终停留在“非善即恶”与“非恶即善”的模式上,从而忽略了事物复杂状态的呈现。80年代如此,90年代以后,甚至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十七年”文学要想进入文学史,并且不是以怪异的面目进入文学史,那么史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许多学者著文论述过,在此一笔带过,不再赘言。
在近年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是思维习惯)值得警惕,那就是不顾历史情境、随意臆测历史的趋向。“十七年”文学自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情境,比如长期战乱局面的结束、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以及整个社会昂扬、乐观、跃进的精神风貌等等。“十七年的作家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参差不齐,但大都经历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战争,经历过抗美援朝,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因此,当时许多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和流露的情感并不一定就是“虚伪的”、“做作的”。作家也并非圣贤,也不能保证洞穿一切,对于后来被历史证明的一些荒谬之举也难免曾经欢欣鼓舞地摇旗呐喊过。但是,现在的许多学者不知是为了谴责当时政治的“非人性化”,还是为了给作家寻一个借口,从而彰显作家的与众不同,往往将作家的真情实感归结为政治的强迫,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拿赵树理的小说来说,赵树理本人曾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但是许多人偏偏无视于此,将赵树理的许多和现实紧密相连的作品归为应景之作,认为是作家无奈状态下的写作。这种判断无疑是有悖于时代和作家个体精神的。归根到底,对“十七年”文学的判断的落脚点还是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
如本文开篇所言,当代文学史写作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才成为近年来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具体到“十七年”文学史写作,其复杂性又大为增加。因为对“十七年”文学现在也是争论颇多,见仁见智,尚无定论。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十七年”文学在进入文学史的过程中,还要不可避免地经历诸多磨难。